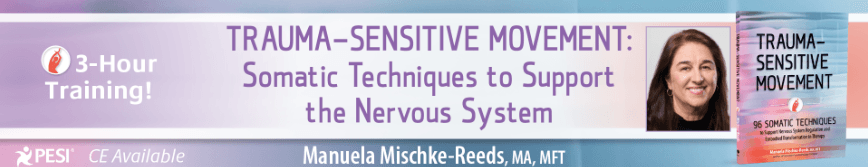接到新個案的時候,很常會被問到:「明明事情已經過去或過去這麼久了,為什麼身體還是會重現當時的緊繃、恐懼感,甚至會在相似的情境下,毫無預警地再次湧現那些不舒服的感覺?而且我理性上明明已經接受、理解了,覺得已經安全地『過去了』,為什麼還是這樣?」或是:「我知道現在遇到的壓力事件引發很多恐懼、焦慮、痛苦,但這和我的過去有什麼關係?我覺得我的過去很好,沒有問題,身體沒有反應有什麼問題嗎?」
這些疑問的背後,其實與我們神經系統的發展和運作方式息息相關。我們的神經系統從受孕初期就開始發展,到了妊娠中期和晚期,所謂的「內隱記憶」就已經開始運作,默默地記錄著我們感知到的外部事物、身體的感覺、當時的原始情緒,以及我們做出或沒有做出的無意識行為等(例:玩臍帶的觸覺經驗?)。這些內隱記憶會再進一步被編織連結,形成我們對世界的預期和反應模式,也就是「心智模型」或「基模」。順道一提,目前也有研究認為,所謂個體的「氣質」(像是高敏感)——其實就是神經系統對刺激過濾的傾向,而這樣的傾向,很可能就根植於此時幾乎完全發育的腦幹。
我們神經系統的主要工作之一,是維持身體內在環境的穩定,也就是所謂的「恆定性(homeostasis)」。為了因應來自外界(例如溫度變化、危險信號)以及內部(例如飢餓、疲勞、情緒波動)等刺激,我們的自主神經系統(Autonomic Nervous System, ANS)會自動調節心跳、呼吸、血管收縮、消化吸收、免疫、激素分泌等多種生理功能,幫助我們保持動態平衡。
當我們感受到壓力刺激時,「尋求社會連結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保護策略。透過 Stephen Porges 提出的「神經覺(neuroception)」概念,神經系統會在無意識層面掃描周遭的聲音、表情、動作、氣氛,判斷當下的情境是安全、危險,還是生命受威脅,並調整我們的神經狀態與行為反應。與此同時,我們的大腦還會透過「鏡像神經元(mirror neurons)」去模擬、理解他人的行為、感受與意圖,這使得我們在與他人互動時,能夠快速同步、產生情緒共鳴,也幫助我們決定要怎麼回應、保護自己、建立連結。
要更深入地理解這些反應如何影響我們,Polyvagal Theory(多元迷走神經理論)提供了一個很有幫助的框架。這個理論指出,迷走神經並不是一條單一的神經,而是由三個演化上不同階段發展出來的神經系統構成:腹側迷走(ventral vagal)、交感神經(sympathetic)、背側迷走(dorsal vagal)。當我們感覺到安全、可以連結時,腹側迷走神經系統會啟動;當我們感覺有壓力、還有餘力應對時,交感神經系統會接手,啟動戰鬥、逃跑、討好等求生反應;當我們感受到壓倒性威脅、已經無力抵抗時,最原始的背側迷走神經系統就會啟動,讓我們進入一種凍結、壓垮、解離、與自己斷線的狀態。
從這個角度去理解,「創傷」其實往往發生在腹側迷走神經功能喪失、無法維持社會連結和安全感的時候,因為我們的身心能量被迫轉去支援求生。那種「我可以應對」和「我無能為力」的差別,反映在神經系統上的運作模式,也就是我在圖上標示的 “I can…” 和 “I can’t…” 的狀態轉換。
其中,「解離」這個現象——也就是麻木、空白、與身體或情緒分離的感覺——很常與背側迷走神經系統有關。當個體感受到極度無助、無法逃脫的情況時,這套系統就會讓我們關機,進入「凍結」模式。如果這樣的狀態持續太久,就會變成一種習慣,導致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感覺變得遲鈍,或無法分辨現在的安全與危險。
根據 EMDR 中的「適應性訊息處理模型(Adap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, AIP)」理論,當壓力經驗無法被好好處理時,與之相關的感覺、情緒、信念、畫面等會被卡在一個未整合的狀態,形成「非適應性記憶網路」,也就容易變成後來反覆出現的痛點。我們所說的「處理」,其實是指「是否達到適應性」。舉例來說,小孩曾經被大人責怪:「我這麼丟臉都是你害的」,如果當時沒有人幫助他釐清和理解,他可能會內化出「大人的情緒是我的責任」這樣的信念,在日後的人際互動中不敢做自己、自我價值感低落;相反地,如果這個經驗後來有機會被重組,他可能能夠發展出這樣的信念:「大人的情緒是大人的責任,而我的行為需要被引導,不是被羞辱。今天如果對方又要我為他的情緒負責,我已經知道那不是我的責任,我只需要好好照顧我自己的感受和行為就可以了。」這樣的信念能幫助我們建立清楚的界線,也更容易維持穩定的自我價值。
也因此,當現在的情境在神經網路的底層,與過去某些未被妥善處理的經驗在感受、壓力模式、感官記憶或情緒基調上產生共鳴時,那些沉睡的記憶就可能被喚醒,身體也會再次做出當時學到的反應。而如果當下情境沒有觸動那些特定的神經網路,或是強度不足以喚醒它們,那麼這些記憶就可能暫時安靜下來,不一定會有強烈的身體反應。但這並不代表這些經驗已經被完全處理好。
早期的依附關係經驗,也會深刻影響我們神經系統的發展,特別是迷走神經系統的調節能力。不過這部分我想以後放在《安全感》那篇再深談。
總之,療癒創傷的過程,是要幫助我們把能量慢慢帶回腹側迷走神經系統,也就是安全、連結、有餘裕的狀態。這通常需要穩定的身體連結、可靠的關係支持,以及重新理解那些記憶的機會。療癒的過程並不是消除創傷經驗,而是從身體到心理完全知道:「我,在這個當下,有力量給自己安全」,並鬆動那些非適應性的信念與模式。透過正念練習、身體取向的經驗療癒、修復性的人際互動等等,我們可以重新建立與自己身體、情緒的連結,找回那份「我可以好好活在這裡」的安全感。
神經元外部連結: